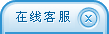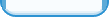陈健民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副教授。他曾是《民间》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也是现时香港“占领中环”行动的积极筹备者。他主张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方面需做出平衡发展。NGOCN记者上周有幸于珠三角公益慈善周首届义工交流营开营期间,邀请到陈健民先生作访谈。
记者:首先问一下陈老师,“公益”与“慈善”之间有什么区别?
陈健民:“慈善”是一个很传统的观念,往往是指拥有比较多社会资源的菁英阶层,利用他们的资源去帮助其他弱势者,但往往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即纯粹是社会的强者帮助弱者。而当我们谈到“公益”的时候,从理念上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因为我们要认识到,之所以会有人处于这么弱势的位置,往往是因为他们得不到一个平等的发展机会,而让他们陷于弱势的环境。一个做公益的人,除了做传统意义上的募捐、服务等慈善行为之外,也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才能让受助者得到一个平等的发展机会。例如,他可能要从事一些与教育相关的工作,让受助者拥有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或者他可能要从事一些倡导的工作,令现行的制度得到改善,以至于让受助者得到平等的机会去发展自己。所以公益是一个更加完整的概念,理念上它强调双方的平等,而服务上它强调让对方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改变制度环境。
记者:内地的民间组织普遍是通过向基金会申请资金,或者由政府购买服务,或是创办人投入自己的财产让组织得以运营,而境外的NGO则有不少是通过小额捐助获得运营资金,为什么在内地这种小额捐款流行不起来?而这两种筹资模式它的利弊在什么地方?
陈健民:我不觉得中国是没有捐助文化的,我们的研究显示早在明清年代已经有不少通过演戏或其他形式去筹款的活动,而不论儒家还是佛家的文化,都有不少是关于慈善的内容在里面,从传统还是历史上我们很早已经有慈善的做法,所以我不认为是文化的障碍所导致。现在这种障碍主要是制度上的障碍,例如内地根本不容许NGO进行公共筹款,捐款者也不能获得税务减免等等。同时这六十年以来很多慈善的理念已经被扭曲,例如大家都习惯了官方主导、从上而下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种官本位的思维扭曲了以往的慈善理念。还有一个信任的问题,大家都不知道哪些机构不会乱花你的捐款,哪些机构有能力运用你的捐款去解决问题,民间机构要面对整个社会对它们的误解。同时NGO在内地遭受这么多年的打压,它本身也很难发展出这种筹款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
再说到不同的资源来源会产生什么影响,先说政府资助,其实有很多国家的NGO都是依靠政府的资助向社会提供服务的,香港做社会服务的机构当中,70%的资源是由政府供给的。机构由政府供给资源的好处是资源较为稳定、充裕,从理念上来说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政府只是税收的托管者,它必须用来开展公共服务,而NGO正是开展公共服务的机构,所以它使用政府的资源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但依赖政府供给资源的问题在于,一个NGO除了要提供社会服务之外,它同时还负有监督政府、倡导政策的责任,而过分依赖政府资源的组织不免会失去这种能力,所以我会觉得不必太羡慕那些能拿到很多政府资源的组织。而民间捐款的特点是分散,它的缺点是不稳定,优点是靠民间捐助生存的机构可以保持自己运作上的自主性,因为很少有捐款者他的影响力可以大到足以影响整个机构的运作。一个组织较为健康的状态应该是能通过多渠道去获取资源,民间捐款有一些、政府供给有一些、企业资助也有一些。至于资源的比例则要视乎机构的使命,例如乐施会就坚持不接受企业捐款,它们不想受到企业影响他们的方向;一些机构会拒绝某些企业的捐助,例如烟草商。机构的使命决定了他的合适筹款对象,我希望NGO能学会通过多元化渠道去筹款。今天还有一些机构自己办社会企业,去为自己创收,令自己更加独立自主。多元化就能让自己拥有更多独立自主的可能性,不受任一方所控制。
记者:以你的观察来说,现时内地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支持,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陈健民:我觉得首先是要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让NGO可以生长起来,这一点很重要。现时政府想孵化一批NGO,但用朱健刚的说法,NGO需要的是一个野生的环境,而不是一个圈养的环境。然而我认为野生的环境也不能太恶劣,让这些组织一出来就死掉了,若能将筹款的领域放开,那么这个野生的环境就不至于太恶劣。还有就是给予NGO一个法律上的地位,让它们可以比较自由地筹款。还有就是让相关款项享有免税待遇。
第二就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公益的发展与公益人才的培养很有关系,例如美国,已经有数以百计的课程培育NGO管理人才、专业社工,而这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例如政府应该在高等教育上投放更多的资源在这些领域上,而这恰恰是民间很难做到的。
记者:去年九月在香港与中国内地分别有两次群众运动发生,香港的是反洗脑教育的十天集会,内地的是反日示威,而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强烈的反差。在香港的集会当中有一幕是一个集会人士晕倒了,人群中马上自觉靠两边移动,留出了一条通道让救护车驾入接走病员;而反观内地的反日示威则出现了很激烈的打砸抢等破坏行为,这实在地令人感到气馁,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陈健民:第一,两地容许公民社会发展的环境很不相同。在内地,当官方越是抑压民间组织的发展,那当群众聚集时就越容易出现聚众闹事,当你只有一次机会去表达你的诉求的时候,所有的诉求就会一次过爆发出来,从而很容易令行动走向激进化。反而当民间有空间持续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懂得谈判、懂得有进有退,那么群众运动就不至于太激进。经验总会显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总比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要好。
第二,回到两个运动本身,香港的反洗脑集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参与,我从未目睹过有这么多的中学生亲身来到运动的现场,还有大学罢课那天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来到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而且还登山来到图书馆前的百万大道集会。但内地反日示威所发生的事件却是很复杂的,它不是纯民间的群众运动,而是当中掺杂了很多非群众的干预,例如不难发现一些单位在休息日雇车把示威者载到现场,而当中的某些打砸抢场景甚至已经可以称之为动乱了,但这些似乎都得到了官方的默许。
其实类似“反日”这类运动在内地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这表明官方一方面很想有一些表达民族主义的运动,你想像一下我们今天的政府,它已不是使用共产主义作为支持执政的意识形态,若靠经济发展作为支柱的话,经济发展会有起有落,所以必须找到另一根支柱,那就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一方面,政府是很希望藉着这种社会动员,去表达一种爱国心,反日反美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它对维护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是非常有好处的;但另一方面,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走得太尽的时候,又会令国家在外交上陷于被动,所以当它发酵到某个位置的时候,政府又很想控制它,但民众的情绪却不是那么容易调控的,所以又很容易失控,“擦枪走火”,然而国家又很鼓励这种民粹式的民族主义存在。所以它跟一种很有组织、很和平的公民社会理念,背后的内容是很不相同的。而且当政府要压制这种原来它所支持的民粹式民族主义的时候,往往会引发群众的不满、反抗,甚至发生冲击政府机关等倒逼政府的群众事件。
记者:你曾经写过《走向公民社会》一书,按你的观察,中国内地的公民社会处于哪一个阶段?作为内地的民间组织或是个人,在这一阶段可以做什么?
陈健民:我经常说希望公民社会首先是求生存,然后是独立自主,接着产生对于社会改变、政策改变的影响力。若看回这三个阶段,内地的公民社会其实还在第一跟第二阶段之间挣扎,离促进社会改变、体制变革、监督政府、监督市场……,我觉得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路。现时内地多数的民间组织处于艰难的生存阶段,可能下一年就会无以为继,少数能处于发展阶段,独立自主阶段,但若要与政府取得互动,促进社会进步,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谈到这个阶段我们有什么可以做,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庆幸来到这个大时代,走在时代的前面。或者你会遇到很多的误解,如父母的不理解,朋友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选择,但当你意识到中国要走一百年才能步进一个文明的国家,即首三十年发展政府、后三十年发展市场、未来三十年发展公民社会,我们刚好在未来三十年的起点上,那尽管我们会得到很多的误解,要有心理准备会遇上很多困难,有时会被打压,然而这时代的先行者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觉得要感谢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让你的人生有了更大的意义,当你在这个时代能够投入进去,那么就会为后面几十年铺平了很多道路,到时的路就会好走很多。特别是未来的十年,真的是很需要一些理想主义者,一些有理想、很坚毅的人去开拓,才能开拓出往后二十年的道。很多人的人生好像很平淡就过去了,他们经常说:“我很想生活在像五•四那样的大时代。”那我就会跟他说:“你现在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一个公民社会开始的大时代。”